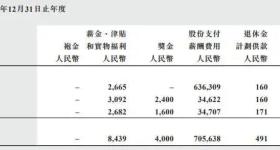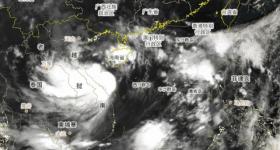“原本没抱什么希望,没想到成功给孩子争取到了一笔生活费。”7月16日,年过七旬的崔爹爹讲述自己为孙子争取胜诉权益时,语带感激。崔爹爹的手里,是一份早已泛黄的判决书。
2007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,夺去了崔爹爹儿子的生命,只留下怀孕的儿媳和年迈的老两口。肇事者耿某对车祸负全责。当时,法院的判决除了明确肇事者耿某其他赔偿金外,还明确:胎儿一旦出生为活体,便可依法享有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请求权。
2008年,儿媳妇马某顺利生下小宇。其后,马某作为法定代理人,于2009年5月通过法院判决,成功为小宇主张到被扶养人生活费2.8万余元。
然而,判决权益尚未兑现,马某就转身离去,从此杳无音信。16年来,小宇由崔爹爹和老伴儿拉扯大。两位老人并不知道有一份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判决书。
直到最近,崔爹爹和老伴儿整理房屋时,才发现这份沉睡了16年的判决书。想着自己和老伴儿一天天老去,能提供给孙子小宇的越来越少,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崔爹爹拿着民事判决书,走进当年审理此案的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,申请执行。
面对老人的执行申请,被执行人耿某提出异议:本案早已超出两年的法定申请执行时效。
法条清晰而冷峻,案件似乎已经难有转机。
“孩子因为车祸从未感受过父爱,随后又被母亲遗忘,如果生活费主张得不到支持,无疑是对他的再一次伤害。”执行法官刘樊意识到,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执行异议案件,更是一场关于未成年人权益的“保卫战”。
在多次翻阅案件卷宗、查阅相关案例后,刘樊发现: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本质,在于满足未成年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,这种义务类似于“扶养费请求权”,不会随着执行时效的“过期”而消失,即便看似失效了14年,但要求给付仍具有合理性。
此案中,小宇作为未成年人,母亲失联,崔爹爹和老伴儿作为实际抚养人,他们既非判决载明的权利人,也非法律规定的法定代理人(生母仍健在),因未知胜诉事实,所以未申请兑现权利,并非怠于行使权利。
法律虽对怠于行使权利者作出时效限制以敦促警醒,但此种限制不应针对因年幼尚不自知的未成年人。
 协商现场
协商现场
“若是直接驳回执行异议,依靠强制力兑现一份迟来16年的判决,未必能真正弥合争议、化解积怨。”刘樊转而向被执行人耿某讲述小宇的不幸,以及崔爹爹老两口的不易,同时阐明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法理与伦理基础。
最终,被执行人耿某认可了自身责任与孩子的应得权利,双方经协商达成和解协议。耿某当场履行了当年的判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