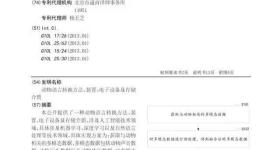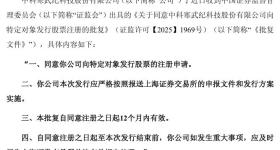520、1314、521……这些藏在转账记录里的暧昧数字,竟是丈夫向第三者输送夫妻共同财产的“暗语”。
7月21日,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,夫妻共同财产,个人无权擅自处置,第三者需返还84万余元。剩余部分款项因涉及工程款项需另案处理。
蹊跷转款——丈夫8年时间给对方转账214万,其中多笔520、1314
1995年,王霞与张超登记结婚,婚姻关系一直存续。2023年,王霞在核对家庭财务时,发现丈夫张超的银行、微信及支付宝账户存在大量异常转账,收款人均为刘丽。更让她心寒的是,这些转账中,2016年3月30日的520元、2016年4月15日的1314元、2019年2月14日的520元等多笔款项,金额特殊,明显暧昧。
面对妻子的质问,张超承认从2014年起就和刘丽认识,这些年陆陆续续转了不少钱。王霞彻查后发现这些年丈夫共向对方银行转账185万多,微信转了24万多,支付宝还有4万多,加起来达214万多元。
至此,张超向妻子写下承诺书,承诺“与刘丽一刀两断,永不来往”。为了挽回损失,王霞找到了北京天池君泰(西安)律师事务所的赵寅律师,“她当时情绪很激动,反复强调那些钱是夫妻二人多年辛苦攒下的共同财产,丈夫无权私自处理。我们明确告诉她,根据《民法典》规定,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,张超的行为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,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。”
一审认定——双方存不正当关系,个人无权处置夫妻财产
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的审理中,赵寅律师明确提出:“根据《民法典》,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权,张超在婚姻存续期间未经王霞同意,将大额财产赠与第三者,既侵犯了王霞的财产权,也违背公序良俗,该赠与行为应属无效,刘丽必须全额返还。”
刘丽辩称这些转账是“商业合作所得”,并提交了张超出具的欠条和项目合同,声称自己为张超的公司跑业务、做项目,款项是提成和工程款。
但法院审理发现,这些证据无法充分证明款项与合法商业往来的直接关联,且多笔“520元”“1314元”的转账明显带有情感赠与性质,结合张超的承诺书,足以认定双方存在不正当关系。
2025年1月,一审法院判决:张超对刘丽的赠与行为无效,刘丽需向王霞返还159万余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。判决明确指出,法律保护夫妻共同财产,否定任何以不正当关系为基础的财产赠与。
二审判决——部分款项另案处理,84万需追回
刘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,以“部分款项涉及工程款”为由减少返还金额。
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,重点核查了2022年后的转账记录——此时刘丽确参与张超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相关项目施工。
法院最终认定:2022年后的部分转账可能与工程款相关(刘丽已另案起诉公司主张该部分款项),暂不纳入本次返还范围;但2022年前的转账及明显带有赠与性质的款项,仍应返还。同时,扣除刘丽已退回的521元及向张超的转款3090元后,判令刘丽返还84万余元。
值得注意的是,二审改判并非“帮助第三者减少损失”,而是基于“工程款与个人赠与需区分认定”的法律原则,对返还范围作出精准界定。法院明确表示,王霞可在工程款纠纷审结后,就剩余争议款项另行起诉,继续维护自身权益。
王霞的代理律师赵寅说,这起婚外赠与纠纷案,折射出婚姻关系中财产处分的法律边界与司法实践的复杂性。丈夫多年间向第三者转账,妻子通过诉讼维权,最终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赵寅称,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,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处理权,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时,需双方协商一致。丈夫擅自将大额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,违背公序良俗且侵犯妻子财产权,赠与行为自始无效。这一案例警示我们:婚姻中任何一方都不应擅自处分大额共同财产,婚外赠与不仅违背道德,更面临法律上的返还风险;作为配偶,若发现类似情况应及时留存转账记录、资金来源等证据,以便在诉讼中清晰界定财产性质;而接受赠与方亦需警惕,来源不明的大额款项可能因赠与行为无效而被追回。
(文中当事人为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