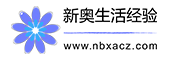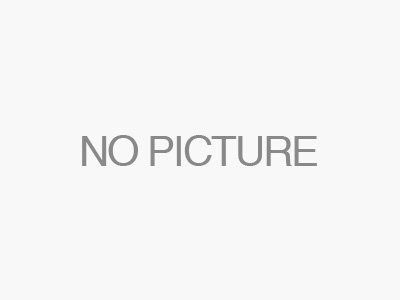时至今日,唐琪还在等待法院判决。
“2024年春天的时候,警方说部分涉案人员已被抓获引渡至国内。”唐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他是北京一家私募基金创始人。
2023年上半年,他与两位合作伙伴受邀前往菲律宾谈生意,对方声称自己是当地华商,要向唐琪所在的私募基金投资数亿元。
他和两位同伴先去了新加坡,见到公司高管。随后,对方又邀请三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“见一见背后的大老板”。唐琪因签证原因,计划稍晚两日前往马尼拉与同伴会合。两位同伴出发后就此失去音讯。
两天后,同伴家属收到绑匪讯息:1300万元赎金,否则撕票。唐琪怎么也想不通,这位大老板是由一位公司老客户介绍来的,怎么会是绑架团伙?
回国协助调查后,警方告诉唐琪,两位同伴直至一周后才被释放,两人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恐吓、虐待、围殴。绑匪发来的照片显示,男性合伙人被打得“面目全非”。唐琪说,“一位警官安慰我,人能回来就好,这类案件最怕的是钱拿了还被撕票。”
由于此前案件一直处于侦破过程中,唐琪没有和同行谈起,他以为自己的案子只是个例。直到2024年,他才得知,朋友郑凯也被人骗去香港,对方甚至邀请朋友前往公海游船度假,但郑凯最终没去。郑凯也是一家私募基金创始人。
“根本没意识到这是骗局,直到香港京都念慈庵发了公告,问了一圈,发现不少人都中招了。”郑凯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,这伙人假扮香港京都念慈庵公司谢氏三兄弟,以投资私募基金为由诱骗当事人前往中国香港、新加坡、东南亚等地,对基金经理敲诈勒索。
2025年4月,郑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提醒同行,并建立了一个受害者微信群,群内有十余位上当受骗的私募基金经理,被骗金额从数万元到120万元不等。但郑凯知道,受害者数量远不止这些。一些同行即便知道被骗了也不愿进群,“一是觉得丢人,基金经理竟被这么低级的手段骗到了,还有人怕投资者问责,公司的风控是怎么做的。”
骗子们的套路并不复杂:冒充知名商业家族联系私募基金,以协商投资的名义将人骗至香港或新加坡,在会餐期间提议打牌、设牌局出老千诈骗资金,最后邀请当事人到东南亚公海邮轮游。
“基金经理们有了自己的专属妙瓦底。”郑凯自嘲。
1
"请君入瓮"
2024年1月,北京一家量化基金合伙人章则收到一条微信好友申请,对方自称香港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(简称念慈庵)的员工。
“第一次联系后只是要了一些产品介绍,大概隔了一周,突然问起近期有没有到香港出差的打算,这就把他们老板‘谢总’引出来了。”章则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。
谢总全名“谢国明”,自称念慈庵谢氏家族三弟,上头还有两位哥哥,掌权家族企业的是大哥谢国昌。这样的邀约,章则每个月都会碰到几次,因此并未设防。之后双方偶尔电话联络、谈一谈投资意向,两个月后,章则动身前往香港,“聊一聊也没什么损失嘛”。
2024年3月11日下午,双方在香港海港城边上的一家餐厅见面。谢国明穿着一件POLO衫和西装长裤、斜跨皮包,出现在章则面前,“看着没有老板的架子,很随和”。
对方做过功课,知道章则公司另一位合伙人在香港金融圈待过,分享了谢家投资越南房产的经验,还有对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的看法,要知道在当时业内DeepSeek还只是一个小众名词。
“从谈吐来看像是个高净值客户,而且言语间很诚恳,介绍了两位哥哥各自的行事风格,说如果将来见面,千万别觉得不习惯。”回想起来,这也是骗子为了引出下一轮骗局的话术。
真正吸引章则的,是对方表示自家在内地有一笔6亿元的投资,几年前计划在内地设厂,但因疫情耽搁了,这笔钱也就一直空置,现在想先拿一个亿来试水内地的投资市场。对章则这样的中小型私募而言,单笔过亿的投资已经算是大客户,但是“谢国明”坦言自己只是牵线,真正拍板的是二哥“谢庆彦”。
念慈庵的总部设于中国台湾台北市,法定代表人谢国昌(大哥),公司董事中有多位谢家子女,包括谢庆彦(二哥),但没有谢国明。综合多家媒体报道,香港京都念慈庵创始人谢兆邦在香港和台湾各有一房子女,三兄弟是台湾二房所出。
双方约定第二天在铜锣湾见面。对方还给章则吃下定心丸,跟“二哥”聊天只是走个过场,这笔投资基本算是敲定了。章则不知道,第二天的饭局才是专为他设的“局”。
“二哥”戴着金丝边眼镜、身高不到170cm,看着斯斯文文。他的身边还有左右“护法”,高瘦的白肤男子、黑黑壮壮的矮个男子各一名。
“二哥”操着标准的普通话,介绍高个男子是新加坡某富商的“公子”,矮个儿则在越南开设赌场、在北京很有人脉。双方边吃边聊了一个多小时,二哥谈吐间,算是基本敲定了合作意向,计划当天下午就签约。
章则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,因为即便合作失败,自己也没什么损失,“都准备要签协议了,甚至一起去洗手间的时候,(二哥)还关照我要多多照顾三弟,他说虽然弟弟没有决策权,但只要弟弟看好的,两位哥哥会尽量照顾,话语相当真诚。”
准备签约时,对方说要等大哥最后来拍个板,并提议不如边等“大哥”边打牌,骗子这才真正露出“獠牙”。
章则想,既然都快签约了,陪客户玩儿两把并无大碍。每把牌的赌注大约是几千港币,玩的是类似德州扑克的游戏,最大不过输万元港币。一开始几局双方有输有赢,突然某一局中间,“二哥”将一打百元美钞拍在桌上,章则有点慌了,“打太大了,估计得有一两万美元”。
两位护法同样“假戏真做”,甚至写下欠条,要跟“二哥”搏一把。“我看了牌面,自己胜率起码90%,所以我也跟进了。”
这一把,让章则输了近10万美元。“我甚至怀疑过他出老千,牌翻出的时候,对方赢的概率只有1%。”章则这才意识到问题,对方还要求把欠款分开打到三个账户,因为小额账户有转账限制。
三弟“谢国明”看章则神色不对,安慰他说,他们兄弟平时玩得都挺大,但这不影响他们的合作,“二哥”信誓旦旦保证晚上就签协议。眼看他们口中的“大哥”迟迟不来,“二哥”推说下午要开个会,让章则晚上在酒店等他。
直到这时,章则还有些侥幸心理,结果晚上没有任何人出现。章则联系“谢国明”,对方推脱说过两天。章则回深圳,对方说去深圳找他,但又没出现,借口是家里母亲病危要回台湾。一周后,章则被拉黑了。
2
角色扮演
骗子的套路基本一致,以投资意向诱骗基金经理,牌局是第一个诈骗关卡。章则的10万美元不是最高金额,在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的十余起案例中,有基金经理在香港被骗120万元人民币,还有基金经理在新加坡被骗100万元人民币。
骗子的手法总结起来有四步,首先通过私募排排网或者公司座机接触管理人,然后邀约基金经理赴香港酒店大堂或餐厅交流,如果敲定一起用餐,会提议打牌并以出老千的方式诈骗钱财,最后如果牌局不成功,还会介绍在场的两位富商邀人至公海旅游。
骗局的细腻之处,在于骗子会针对不同基金经理扮演不同角色。
比如不会打牌的安丰,对方在2024年4月通过公司座机联系上他,同一拨人,借口、理由、前期接触过程都与章则遭遇的情况类似。因为知道安丰的公司排名较为靠前,对方也做了不少功课,着重了解了公司业务,目的是寻找共同话题、加强双方的匹配程度。
在私募基金行业,投资人是名副其实的甲方,但为了避免资金进出波动影响产品表现,基金经理在接触投资人时也会进行一定的筛选,寻找更合适的资金来匹配其投资风格。
“对方相当准确地推断出我们过去三年的重仓赛道,连行业合规检查的敏感时段都了如指掌。”遇上如此专业的投资人,安丰也尽心地准备宣传材料。在第一次视频会议里,安丰精心准备了四十多页PPT,向对方展示以往的成果和投资逻辑。
安丰做了简单的背景调查,研究了念慈庵近十年产业布局,甚至找到香港中医药协会的理事名单,但这些在跨境诈骗集团面前都是徒劳。“在私募行业,大部分客户都是朋友或者老客户介绍,一个小圈子里,都知道彼此做的什么生意,很少有人会做深入的背调。”
骗子的话术一定是“相见恨晚”,比如安丰表示需要稳定、长期的资金,“谢国明”立即表示自己的资金属于家族办公室(简称家办),都是长期资金,是名副其实的“Old Money(老钱)”。
饭局中,安丰表示自己不会打牌,对方严厉“斥责”他不懂风情,又提出替代方案,声称上述那位新加坡的富家公子家里是做航运的,家里有不少游艇。恰巧近期来一批新游艇,于是邀请安丰出席下水仪式。
公海属于三不管地带,驶入公海的游船不必交纳赌税,不需政府授权,不受法律限制,因此颇受赌徒欢迎。然而由于没有法律保护,公海也成为欺诈、绑票等犯罪行为的多发地。
对方甚至表示如果安丰“识趣”,可以凭借自家人脉帮他介绍其他香港富豪业务,安丰承认有一瞬的心动:“我就这样打进香港的富豪圈了?只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”
安丰最终识别出骗局是靠一个细节:这伙人全程没有询问关于收费的问题。他解释,通常私募会为家办设立单独的专属产品,跟其他市面上产品的费率会有所不同,这需要双方协商确定。
“有关管理费的问题,他们完全没有问,刚开始接触还没必要谈得那么细,可是直到饭桌上要签合同了,对方都只字未提。我主动提了1.2%的管理费加20%的业绩报酬,对方竟然毫无反应,我意识到了不对劲。”
对方还是想把安丰带上牌桌,安丰坚决表示不会打牌,极限拉扯中,对方甚至语气带有恐吓地问,“你不打牌平时玩什么?”安丰说自己只是健身、看书,看安丰“油盐不进”的样子,场面一度变得很尴尬。
“我一开始是本能拒绝,因为真不会打牌。但自己脑子里的警报声不断在响,最后只觉得很失望,我意识到这是个骗局。我说自己下午还要回深圳,在深圳约了朋友,两个马仔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现场的二哥。”
一瞬间,安丰直觉对方几人面色不善,他想到了最坏的情况——自己今天回不去了,“可能下一秒就被绑了,现在回想起来,只觉得后怕”。
所幸对方并没有强迫他,顺势放他离开了,“但凡有人碰第一把,估计没个十几万几十万出不来的”。
3
圈子生意
黄爵是北京一家私募基金的投资负责人,他坦言自己没有走到骗局的最后一步,仅仅是因为运气。
2024年7月,他随对方前往香港喝茶,双方有了初步合作意向,但因为第二天下午要赶回北京,他只给对方预留了两个小时时间。
对方拒绝了饭局。黄爵一开始以为骗子是嫌自己的诚意不够,和其他受害基金经理交流后才知道,原来是没有给骗子留足行骗的时间,“对方觉得你既然都不打牌了,也不用花钱跟你吃饭了,毕竟骗子也要讲究经济效益。”
黄爵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,双方还时不时地沟通投资意向。几个月后,对方突然拉黑了他。
2025年2月,念慈庵公司发布一则公告称:近期发现,有不法分子冒充本公司管理人员,透过虚设私募基金或成立投资项目进行讹诈。本公司郑重声明:上述行为与本公司无任何关系,请公众提高警惕,慎防受骗。
在郑凯统计的受害者中,有半数都遭遇了钱财损失,金额普遍在数十万元及以上。微信后台不断有人向他私信了解情况,“大概率都是受骗上当的,只是不愿意暴露自己”。
为何这类针对高端金融从业者的诈骗屡屡得手?
一个客观原因是,私募基金的业务推广依靠长期合作和口耳相传,大部分客户都是圈内人介绍。这类“熟人生意”的进入门槛很高,可一旦找到突破口,很容易逐个击破。
“国内无论是家办还是私募,至少都是备过案的。双方接触后吃个饭、喝个酒太正常不过,偶尔熟人间打牌也有,但也基本点到为止。之前流行德州扑克,大家也会跟风玩,和客户都是老熟人了,基本不存在防诈需求。”唐琪说。
“我们客户的身家至少都有几亿,谁能想到他们介绍的人还会是诈骗犯?”唐琪记得,被骗回国那会儿,自己看谁都像骗子,同事之间基本没了互信,都觉得别人想害自己。
章则悟出一个道理,自己根本没必要去冒险,“我们这个行业天天见有钱人,但凡守不住内心的都进去了。现在我的想法特别简单,赚自己能力边界的钱,守住自己内心的底线就好。”
4
“最佳猎物”
安丰也曾想过报警,将这伙人公之于众。但熟人告诉他,但各种立案调查、取证极为困难,像他这样没有造成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的,很难立案。还有一些被骗的基金经理,出于声誉考量,只能默默认栽。
要防范这类诈骗,基本只能依靠基金经理个人的职业素养和公司风控体系。
据《新京报》报道,2024年9月,两名中国医疗器械公司高管赴菲律宾工作时,遭遇绑架并被“撕票”。案件的最新进展是,将两名受害者骗至菲律宾实施绑架的“李娜”在韩国首尔落网。
和唐琪的同伴遭遇类似,二人受当地潜在合作伙伴邀请一同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拓展业务,飞机降落不久后即被绑架,支付赎金后仍被撕票。
时至今日,被绑架、诈骗的受害人已从富商阶层,向下蔓延至社会精英群体。
诈骗分子刻意向基金经理们强调“资金闭环操作”“无需公开披露”,正是针对私募机构规避监管审查的心理。南方周末记者对这些受害者进行了简单统计,大部分基金经理在接受邀约时,其所在机构正经历连续两个季度的净赎回。
郑凯试图总结出一些共性,比如行骗者们如何精选猎物。该团伙一般通过私募排排网、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等渠道,精准筛选管理规模5亿-20亿元的中型机构。“这些私募既有募资焦虑,又缺乏跨国尽调能力,是最佳猎物。”
“接触国际资金,中小私募肯定没有经验的。经过这次之后,这种钱我也不想要了,还是要等真正靠谱的介绍过来才行。”唐琪说。
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,2024年全年,私募基金市场上的管理人数量、产品数量、规模三者均遭缩水。2024年,中基协合计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1502家,平均每月注销私募机构约125家。
几位受访人不约而同提到,整个私募基金行业正在加剧洗牌,竞争博弈已经相当严苛。这或许也解释了,为何部分基金经理选择铤而走险、在没有详尽背调的情况下开门营业,让诈骗分子有了可乘之机。
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前,“谢国明”等团伙仍在作案,只是换了身份,一会儿是余仁生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董事“余羲鸿”和投资部经理“荘龙祥”,一会儿是马百良药厂的高管“马泰宏”,并且仍在接触基金经理群体。余仁生和马百良均为知名传统中药企业。
南方周末记者尝试拨通“谢国明”等一伙人的电话,多个号码均已经在念慈庵发布公告后注销。
(应受访者要求,唐琪、郑凯、章则、安丰、黄爵为化名)